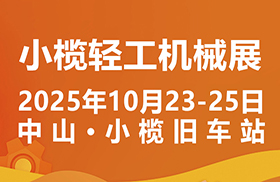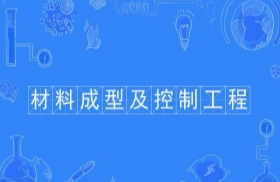在东莞,“机器换人”其实早就开始了。大朗从2008年起掀起的数控织机潮就是其中典型。2009年底,大朗数控织机不足一万台,经过几年的推广,如今数控织机使用量已超过4万台,共节省人力20万人。
租赁经济是东莞基层村组发展一个较为普遍的模式。就在东莞机器换人如火如荼地吹响号角之时,基层却在担忧:如果企业都用机器把人换走了,村组社区的房子租给谁住?对此,东莞市机器人技术协会副会长罗百辉表示,机器换人将是一个长期、渐进的过程,其中并不意味着企业大规模减员,甚至还会催生新的就业创富机会,成为基层经济转型的一个机遇。更重要的是,单靠廉价劳动力和吃租分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,机器换人与村组经济转型都时不我待,其中或许会有阵痛,但脚步一刻也不能迟疑。
罗百辉明确指出,机器换人是东莞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。机器换人将促进产业升级和人的升级,从而推动东莞整个城市的升级。只是在这个过程中,伴生的社会问题需要未雨绸缪。政府在大力推动机器换人的同时,还要运用好和完善配套政策,进一步激发基层创新、创业、创富的激情,破除路径依赖,助推东莞成功转型升级。
人机的升级
机器换人不仅可以解放更多劳动力,还可以创造更多新的、附加值更高的岗位,如机器维修、研发、销售、培训等,这将促进东莞产业和工人同步升级。
38岁的陕西汉子戴朝智,看护着一人多高的自动包装机,机械手臂灵巧地将一摞重达几十斤的瓷砖打包,由码垛打托机器人垒起来,工友开动叉车将其运走偌大的车间里只有不到20名工人在看管机器。
东莞唯美陶瓷制造车间里,这样的一幕近日被媒体广泛报道。不久前,市委副书记、市长袁宝成曾在此做机器换人专题调研。
这样的现代化工厂,与我国制造业留给人们的刻板印象似乎毫无关系。在东莞大多数工厂里,通常能见到成百上千名工人在流水线上埋头苦干。唯美陶瓷制造车间里,也曾经人满为患,两三百工人在车间里人工磨边抛光、捡砖打托。
变化发生在戴朝智被当做重劳力招进的2007年。当时,唯美陶瓷董事长黄建平出国考察后,从国外购买自动化设备,前前后后花了2亿多元,阶段性完成机器换人的生产转型,节约用工2200人。
推行自动化的时候,工人中存在不同的声音,有的担心文化低学不会,有的怕被机器取代了。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明确传达了厂里的意思:愿干体力活,有新厂和生产线可以安排岗位;愿意转型看机器,可以到唯美学校学习,简单、包会。唯美东莞厂区机器换人,做到了减员不裁员。
戴朝智和几个年轻的工友一起决定学操作机器。培训人员把操作规则都编成口诀,让他们熟读并实践,还不忘贴在机器上以供忘记时一看就会,出现问题按铃报告。
戴朝智清楚地感受到,转型后的工作轻松、体面:月薪从原来的3000多元涨到现在4000多元,加把劲还能上到5000元。新成长起来的产业工人,成了机器换人过程中最直接的受益者。
戴朝智的经历,只是东莞机器换人大潮中的一个缩影。机器换人直接带来的是城市人口素质的一次大提升。
机器设定一个程序,调节、维修等,也都是要人的。这些新岗位劳动者要具备一定的技能和文化知识,简而言之,就是把简单加工型的劳动者,变成技能技术型人才,即高端蓝领,这正是我们需要的。厚街当前正在积极推进机器换人,该镇党委书记万卓培表示,以产业发展规律来看,使用新机器、新技术时,直接操作工人会减少,但研发、销售、服务、培训部门的就业机会就会增加,对东莞而言,实现了产业升级与人的升级同步。随着人的升级,收入的增加,也会为当地消费作出更多贡献,对社会的转型升级发挥良性促进作用。
催生新业态
大朗推广数控织机过程中,从事数控织机生产、销售以及售后服务的企业或机构等形成了数控织机一条街,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。
在东莞,机器换人其实早就开始了。大朗从2008年起掀起的数控织机潮就是其中典型。2009年底,大朗数控织机不足一万台,经过几年的推广,如今数控织机使用量已超过4万台,共节省人力20万人。
大朗镇的繁荣并没有因此有丝毫减退。一般来说,一台数控织机能顶6-8个人,一开始我们也担心:换人会不会使房租减少?要知道,巷头村80%的集体收入来自于物业出租。后来才发现,这个担心是多余的,你看看外面的商铺,哪一个是空的。素有天下毛织第一村的巷头社区居委会里,负责企业工厂的村委委员陈暖根说。
巷头居委会门外的大街上,两排商铺前车水马龙。今年41岁的刘传富租了其中的一间商铺。以前用人工手摇机拉拉扯扯,一天只能生产四五件,现在一个人就可以看6-8台机,一天下来可以生产200多件,而且还没以前那么累。从工人变成老板的刘传富说。
2002年,刘传富从安徽到大朗巷头村,从杂工做起,十年间做到了工厂一个部门主管,工资也从每月450元涨到了6000元。这时,工厂里已经开始用数控织机,换下来的人,大多进入缝盘、后整等工序,这些工序正缺人手。
还有不少比刘传富更老资格的工友们,纷纷离厂单干:他们往往三五个人,凑点钱,买下十几台数控织机,租一个铺位,接大厂的订单做毛织加工。
发不了大财,但自己当老板,总比给别人打工强。2012年,动了心思的刘传富拿打工攒的十几万块钱和亲朋好友的借款,买了几台数控织机。亲朋好友全上阵,一年多下来,他的这个小作坊一年的人均收入比打工时翻了一番。现在买机器按揭的尾款差不多要还完了,之后就是净赚的了。刘传富盘算着在东莞买一套房子安家,他很庆幸这些数控织机让他创业。
值得一提的是,数控织机热也催生了另一种产业。驱车徜徉在平坦宽阔的银朗大道,道路两旁琳琅满目、鳞次栉比的数控织机大招牌依然分外抢眼,这里已成为华南地区数控织机的集散地。
跻身其中的金龙公司总经理周齐说,高峰期时这里有一百多家从事数控织机生产、销售以及售后服务的企业或机构,大朗银朗路数控织机一条街应运而生,短短几年就造就了数十名百万富翁。金龙在2012年在华南地区的收入超过一个亿,其中多数来自大朗。
大朗巷头的故事,印证了机器换人给基层经济带来了更大的活力。事实上,租赁经济绝不是东莞村组经济发展的唯一选择。凤岗镇雁田早在1988年就成立公司进行投资,近年来甚至走出东莞开展了多元化的投资业务。中堂镇潢涌走的则是一条自办企业之路,发达的集体经济造就了中国造纸名村之名。雁田和潢涌在发展过程中,从来不抗拒技术的升级,也不依赖人的数量的扩张,它们的繁荣和发展却从未中断。
机器换人不可能一蹴而就
机器不可能完全代替人,东莞机器换人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按照有关部门统计,目前,大朗毛织行业已全部完成第一阶段的机器换人。而在周齐眼中,如果说毛纺自动化分三步走,现在大朗只走出第一步。
整个毛纺制造环节主要分为织片、缝盘、后整三大工序,后两个环节均未能完成自动化。数控织机只解决了织片环节自动化,即将原料织成一片片的材料。以往,织片需要9个工人,那么缝盘就得3个工人,后整再配2个,而现在,织片、缝盘和后整的工人配比是1:3:2.
目前,大朗缝盘工人的月工资已经涨到了6000元,刘传富原先所在的工厂晶晖针织有限公司老板陈伟光,有时不得不花两百到三百一天的工资,请刘传富等人帮忙找临时工。一次,为赶货期,他甚至开出了一万五的月薪来招缝盘工人。
周齐认为,织片、缝盘、后整、质检、包装等多个环节,都可以实现智能工厂或无人车间运作,特别是缝盘很有希望机器换人。但目前,全自动的缝盘的机器仍旧太贵且效果不理想,得不到客户认可。
缝盘机也正在等待着一场国内的技术革命。周齐说。曾经,大朗的数控织机就得益于数控织机的国产化。在2004年后,便宜好用的国产数控织机开始大行其道。这之前,数控织机被德国和日本垄断,一台机器需要二三十万元,企业根本无力承担。
问题是从2004年国产化以来到现在,数控织机推广都用了10年,再到整个流水线全自动化,那该多久啊!周齐感叹。
机器换人不可能一蹴而就,机器也不可能完全代替人。比如我们引进了一个项目,叫黄金装备生产基地,一台机器,可以代替十几个人,但最后一个环节还是要人去做。万卓培说。
东莞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坦言,机器换人并非涉及全部企业、所有工序,有不少环节是机器做不了的。东莞还有大量的中小微企业,他们是就业的蓄水池,对于这些企业而言,机器换人还很遥远,技术红利替代人口红利是一个长期过程。
转型升级的信心
机器换人无疑增强了企业扎根东莞就地转型升级的信心,为基层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。
其实,比起机器换人可能带来的工人减少,基层更应该关注的,是如何让企业扎根东莞,就地转型升级。随着劳动力廉价时代的结束,东莞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要么搬迁内地甚至柬埔寨、缅甸,要么转型升级,例如自动化技术。周齐说。
在大朗毛纺机械行业打拼了十几年的周齐亲眼见证了毛纺产业转移:新世纪之初,民工荒在珠三角首次出现。一些港台大厂开始往周边省份布局,有的内地老板也开始将分厂开回家乡。一开始还只是广西、江西、湖南,算是500公里左右,三四个小时的生活圈内,到了2008年后,就开始转移到1000公里以外的湖北、安徽、河南等地了。
今年6月,东莞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全市机器换人行动计划。在外界看来,东莞此举将大大增加企业扎根东莞的信心。现在不是留不留得住人的问题,而是如何让企业扎根东莞发展的问题。
几年前,工人一个月连加班才2000多元,现在不加班一般普工起薪都到了3300元左右。每年春节后,陈伟光最头疼的就是听到工人跟他讨价还价:加300就回来!近三年来,他为此支付工人工资几乎每年上涨百分之十几,说到这里,陈伟光愁眉苦脸。现在,类似毛纺行业已经陷入工人青黄不接,年纪大的工人在缝盘时眼花手慢,而90后并不愿意进入这一行当。
唯美陶瓷相关人士则感到很庆幸,他们早就实现了自动化生产。现在,一些劳动强度高的岗位,工资开到七八千多都鲜有年轻人愿意做,但这一招工难题并没有给唯美造成太大的困扰。
有些产业,如果再不上机器的话,你说还有什么竞争优势?你除了提高人工工资,还有什么手段能吸引人家过来?面对市场消费的多元化发展,设计上很复杂,工艺上也很复杂,用人做不了的时候,就要用机器去做。万卓培说。
周齐说得更为直接:不管你习不习惯、愿不愿意,随着自动化设备价格下降,人工成本上升,二者总会让企业越来越倾向于机器换人,这是历史潮流。他伸出双手,将一手往下压,一手夸张地往上抬高。
学者们也早就看出了这一点。你不要抱怨工人难招,中国工人已经被廉价地使用了这么多年,现在只不过是人口红利宣告结束。近日,在莞商学院一周年论坛上,独立经济学家金岩石告诫台下企业家,在高速发展了30多年后,有些趋势企业必须学会接受。
他认为,流动人口大量集中于制造加工、餐饮服务等附加值较低的产业末端,无法成为未来东莞大城市人口集聚的主干。城市化需要的高层次、高技能人才比例过低,又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新一轮工业化。因此,有必要使换下来的工人加速成长为知识型生产者,奠定大城市人口基石,让机器换人成为倒逼东莞产业和社会转型的一个契机。
机器换人配套政策
机器换人过程中,政府还应运用好和完善配套政策,进一步激发基层创新、创业、创富的激情,破除路径依赖,助推东莞成功转型升级。东莞市机器人技术协会副会长罗百辉认为,部分基层干部群众对机器换人的担忧,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对租赁经济的路径依赖。发达的村组经济,曾是东莞最耀眼的名片。但辉煌的过去,形成的路径依赖,成为东莞村组经济转型升级的思维障碍。事实上,早在东莞吹响机器换人的号角之前,人口红利已经在逐步丧失,租赁经济早已难以为继。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,东莞已经尝过了租赁经济带来的苦头,村组经济转型早已时不我待。
今年6月5日,市委书记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建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:机器换人后,工业吸纳就业能力下降,随着工人的减少,可能对一些村组和村民的租赁收入产生影响。这种影响属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阵痛。长痛不如短痛,我们既不能因为有阵痛就停滞不前,同时也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少、舒缓阵痛。
罗百辉指出,机器换人是东莞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。机器换人将促进产业升级和人的升级,从而推动东莞整个城市的升级。在这个过程中,基层也将享受到东莞转型升级带来的红利,而不仅仅是已然式微的人口红利了。在这个过程中,伴生的社会问题需要未雨绸缪。政府在大力推动机器换人的同时,还要运用好和完善配套政策,进一步激发基层创新、创业、创富的激情,破除路径依赖,助推东莞成功转型升级。